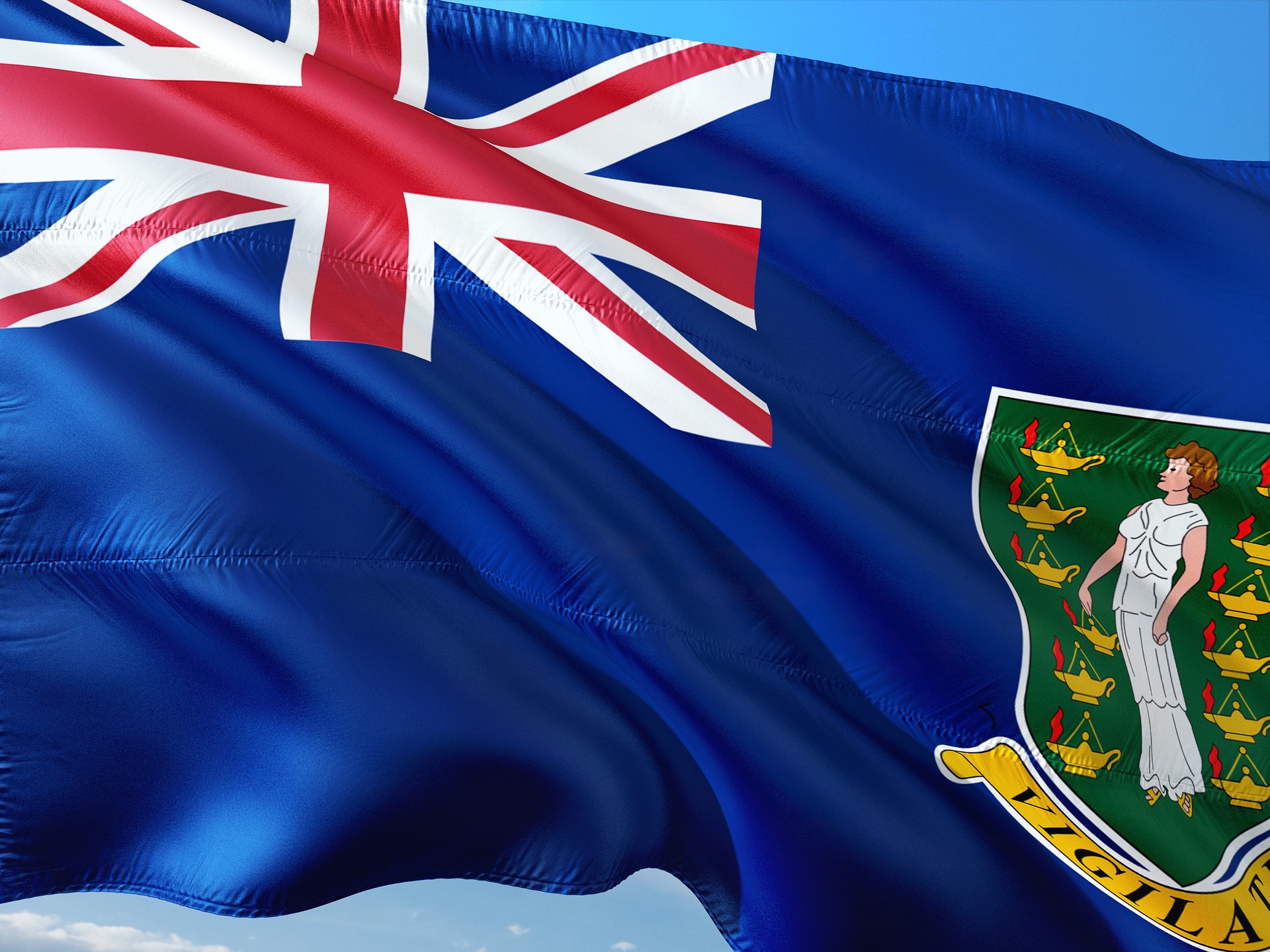从历史背景看,基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的金融业单行法性质与《信托法》的《民法》特别法的性质,以及中国将所谓“信托业”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离出来的现实,中国信托业在分业体制下的定位,直接导致其在机构性质和业务范围方面属于信托公司业规范而非信托业规范的特征,与国际所认可的正统信托业务相比存在内生性缺陷。中国信托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其实质仅为兼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业务,不具备家族信托的基本属性。中国《信托法》在对“信托”的定义中规避了财产所有权变动这一环节是一个明显的佐证。
中国《信托法》中未明确规定“家族信托”的概念,尽管“家族信托(以个人作为委托人,以家族财富的管理、传承和保护为目的信托,受益人一般为本家族成员)”的交易结构并未违反《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其在国内开展并无法律法规禁止,但是,这不代表家族信托在国内开展不存在障碍。事实上,家族信托在我国信托制度下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信托效力障碍”及“税理优势弱化”等本质上的负面影响。
就家族信托的效力而言,由于我国《信托法》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具体情形尚缺乏明确的配套规定,造成信托财产登记中程序性规范的缺乏以及对信托效力理解上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家族信托在中国的开展。
从家族信托在海外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源于有效地规避高额遗产税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开征遗产税虽有趋势,但其实际征收尚不确切,信托活动本身固有的税收策划和节税功能未能得到有效体现,直接导致委托人在中国设立家族信托的意愿不强烈。
那么,中国大陆富裕家族真的不需要信托吗?从资产分布、宏观税负、产业趋势、信托资源等角度,恰恰可以得出海外信托当今在中国“受宠”的结论。
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富裕人群的资产(资金、股权、不动产、动产等)早已经不限于中国大陆单一司法辖区,这直接造成信托事务的处理可能在中国大陆,也可能在海外地区或国家。
其次,中国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产业经济运行分析与建议报告》称,当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高达40%左右,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在中国偏高的宏观税负环境下,中国居民的实际经济福利也存在减少趋势。数据表明,1997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城镇家庭的名义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为11%,农村家庭则为9%,可见居民层面的名义收入也远低于最窄口径计算的税负增速(即:1994年的11%,2003年的15%和2012年的20%),所谓“被逼移民(包括身份和资产)”的叹息并非庸人自扰。
再次,纵观“中国家族企业对中国GDP贡献超过一半、家族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75%”以及“中国大陆84.5%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未来5到10年大约3/4的家族企业面临交接班”这两个现象,再考虑到“仅18%的企业家后代愿意主动接班”、“多数后代更亲睐网络、电子商务、VC、PE”的趋势,不难看出,中国家族企业拟采取有效途径抵御“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可以说是一个“刚性需求”。
最后,中国的国税总局698号文实施以来,某些提前设定海外信托的家族充分利用受益人变动得以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从而一定程度规避或减轻中国税务负担的故事,逐步广泛流传,凸现海外信托在便利性、隐蔽性的积极作用,尤其在进一步扩大中国富裕家庭利用海外信托引导家族资产传承的需求方面存在推动作用。而中国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的规定,更从民事法律关系意思自治的角度给予中国富裕家族设立海外家族信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从以上制度和现象分析,可以认为,海外家族信托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仍将在国人选择资产传承工具中占据优势地位。毕竟,如果中国的信托制度改革在承认和借鉴国际通用理念方面不能运用充分的智慧和豁达,处理好制度设计、配套政策、金融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海外信托通过长期实践所形成的在契约优先、意思自治、人才储备、税收刺激、服务广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依然难以被动摇。